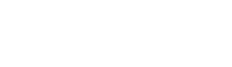陈克勇
在我的感觉中,现代与过去相比,最突出的变化之一,就是交通方便了,不是一般的方便,而是大大地方便了。
我居住的地方金乡,过去是个举步艰难,闭塞的小镇。虽然在明代开始就是个有名的抗倭名城,但那时交通靠什么,除了靠海上的船只,就是徒步了。后来,改朝换代,还是没什么变化。记得我年少时,我外公去南方,经梅峰古道,爬山越岭,就靠双腿,也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到达福州,成为惊人之举。
我青少年时在温州读书,已经是解放后了,但交通基本上没什么发展。连通金乡与温州的是一条长长的水路。
那时,从金乡至温州,往往是半夜踏着月光乘摇摇晃晃的小船,第二天凌晨到方岩(现在的龙港),渡过鳌江,再乘小河轮至平阳,上岸后从铺南走到铺北,再乘小轮船至飞云江南岸,摆渡过江至瑞安南端,疲惫的小腿还要穿过瑞安县城的一条中心长街至北端。这时,已接近正午,饥肠辘辘,吃碗阳春面,千辛万苦的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因为我们看到塘河了,看到了塘河,也就像看到了温州。
后来,金乡至方岩下,终于有了小河轮,但也快不了多少。记得有一年大旱,河水太浅,开不了小河轮,因急事,竟去鳌江乘海船去温州,风吹浪打,大家在甲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,上面盖块油布,活像个难民,许多人(包括我在内)吐得一塌糊涂,叫苦连天。
后来,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,开始有了公路通灵溪。可那是一条据说原来是备战用的,靠山,蜿蜒曲折,从金乡到灵溪竟要三个半小时。到温州可就要5、6个小时了。可有什么法子呢,我那当个采购员,总是天未亮就去南门车站去排队买票。还设法与站长、售票员搞好关系,采购重任在身,急时不得不开后门呀。
苍南建县后,随着金乡经济的全面发展,交通建设亦令人瞩目。
1987年,龙港至金乡的公路建成,长27.82公里,路基8.5米,路面7米。总算可以不必经灵溪去温州了,缩短了不少行程。然而,毕竟这老公路太窄了,负担不了众多的来往车辆。
2002年底,龙港至金乡的龙金大道终于建成,亦称50米大道,基本上按高速公路的要求建设,路两旁有铝合金栏杆,路中间有花坛,间隔相向行驶的车辆。南来北往的车辆,基本上流水般地畅通无阻。我也不知,这算不算重点工程,反正,此大道建成,大大改善了金乡乃至我县的交通环境。
光阴如白驹过隙,弹指一挥间。现在我已无重任,儿女也都已成家,大外孙都中国美术学院毕业,参加工作,会开小车了。儿女们及第三代有的在杭州;有的在灵溪、龙港。
回想起来,社会的发展,有时像蜗牛,有时又像火箭。很难想到,在短短的不到十年中,我们家的四个子女,现在竟有了五部小车,有奥迪、北京现代、别克,还有叫不出名的。
感觉上,地球变小了。节假日,子孙们从杭州回家也仅需几个小时,可以自驾,也可以坐动车。坐动车到灵溪站,也早有小车去接。
虽然只有我们俩老在金乡,但从不感到寂寞。因为交通的方便,儿女们常找点空闲找点时间,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。到时,我也自然会张罗了一桌好饭,但生活的烦恼不大跟妈妈说,工作的事情也大抵不必向我谈。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是有的,也常陪老爸老妈打麻将。赢输无关紧要,也不差这点小钱,图的是嘻嘻哈哈,热热闹闹。天黑了,不想在这儿睡,就开车经龙金大道回龙港、灵溪。只是家里藏有的几瓶酒,都喝不了,因为醉驾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有一次,新加坡的亲戚回故乡。儿子去温州机场接他们。从萧江高速口出来后,再经龙金大道路时,国外的亲戚眼望着车窗外,对龙金大道赞口不绝,感叹不已地说,变化真大呀。许多年前,他是来过金乡的,曾经在方岩下乘小船,问价,答:二元四角。他说:我给你四元八角,你来俩人,双桨划好吗?
真是归心似箭。其实,双桨比单干也快不了一小时,而现在从萧江到金乡也只要几十分钟。
感谢上苍,多亏有了龙金大道。
【编辑:李甫仓】